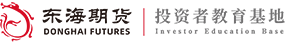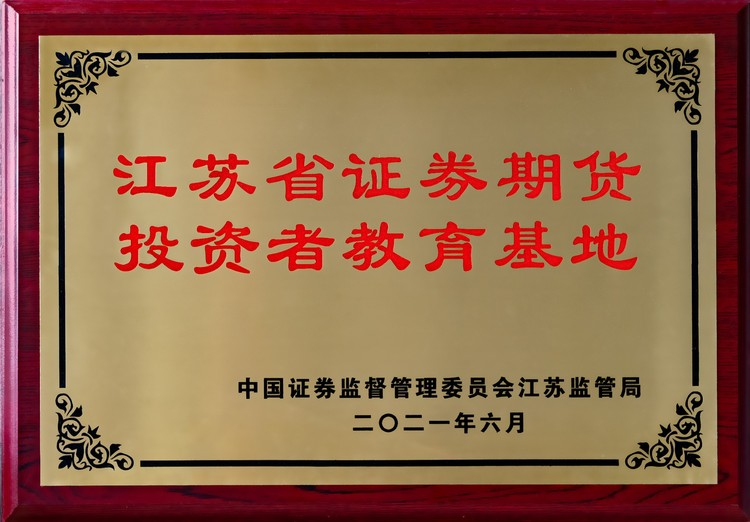作者:桂旭
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理财产品、各类资产管理计划等资产管理产品是期货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期货市场开户管理规定,资产管理产品参与期货市场交易,主要以作为资产管理人的金融机构为资产管理产品申请开立“特殊单位客户”账户的方式进行,以区别于没有资产分户管理需求的企业客户申请开立的“一般单位客户”账户。行业内长期以来存在一种观点,在责任方面将“特殊单位客户”视同法人,认为“特殊单位客户”仅以资产管理产品的财产承担责任。当“特殊单位客户”账户发生穿仓,资产管理人无义务以其固有财产对期货公司承担责任。
近来,有资产管理人申请开立“特殊单位客户”账户,与期货公司风险管理子公司进行场外衍生品交易时,明确要求期货公司承认“管理人有限责任”,如在合同中加入“资管产品仅以其财产为限承担责任”“管理人的固有财产不对资管产品承担任何责任”等表述。在期货经纪、场外衍生品交易等业务中,期货公司及其风险管理子公司属于资产管理人的交易相对方。而在期货资产管理业务中,期货公司本身又为资产管理人。因此,如何认识管理人有限责任,会多方面影响期货公司利益,有必要厘清认识、形成共识。
受托人对外责任的两种误解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认为,根据《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的规定,其他金融机构开展的资产管理业务构成信托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纠纷适用信托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处理。大多数参与期货市场交易的资产管理产品,都属于信托法律关系。故资产管理机构为受托人;投资者为委托人,多数情况下亦为受益人;资产管理产品为信托财产。因此,“管理人有限责任”实际上是受托人对外责任的问题。
资产管理机构常援引信托财产独立性这一广被接受的表述来支持其对信托债权人的有限责任。信托财产独立性指信托财产在信托存续期间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各自的固有财产。根据信托法,在信托依法设立后,信托财产即独立于委托人未设立信托的其他固有财产,受益人对信托财产享有的权利表现为信托受益权,故信托财产独立于委托人和受益人在实践中基本不存在分歧。但对于受托人而言,信托财产免于受托人个人债权人的追索是不言而喻的,但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是否免于信托债权人的追索却充满争议。
争议一方面源于对信托法第37条的理解。该条规定,“受托人因处理信托事务所支出的费用、对第三人所负债务,以信托财产承担。受托人以其固有财产先行支付的,对信托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第一款)。受托人违背管理职责或者处理信托事务不当对第三人所负债务或者自己所受到的损失,以其固有财产承担(第二款)。”很多人将这条解读为信托财产独立性的依据之一,即认为只有当受托人存在过错时,才以固有财产对第三人承担责任,除此之外受托人的固有财产免于信托债权人的追索。在大量信托纠纷案件中,受托人都会依据该条,抗辩第三方债权人的请求。
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误解。第37条第一款规定的是受托人可用信托财产承担债务的情形、方式以及受托人的求偿权,文义中从来无法得出以“信托财产为限”的结论。第二款规定的是受托人不得以信托财产承担债务的情形,即当受托人有过错时,仅能以其固有财产承担责任,不能向信托财产求偿。根据第二款的文义,“受托人过错”和“以受托人固有财产承担责任”之间,显然只是充分非必要的关系。存在“受托人过错”,则可以得出“以受托人固有财产承担责任”。不存在“以受托人固有财产承担责任”,则必然没有“受托人过错”。存在“以受托人固有财产承担责任”,则未必有“受托人过错”。因此结合第37条两款内容,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当且仅当受托人履行管理职责合理处理信托事务对第三人所负的债务或者受到的损失,受托人以其固有财产先行支付的,可以向信托财产求偿。但是,绝对无法得出“只有当受托人存在过错时方以其固有财产承担责任”的结论。
争议的另一方面源于将信托财产误解为财团法人。这种观点将信托类比于公司,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如同经理代表公司从事经营活动,所以信托可以适用法人有限责任的法律规定。法人是法律创设的虚拟人,因此某类实体是否构成法人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进行判断。民法典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信托财产虽然构成财团,但受托人、受益人、委托人和信托财产并非是一个组织,显然不符合法律关于法人的定义,所以并没有法人资格,自然也就不能享受法定的有限责任这一“福利”。
受托人原则上对外承担无限责任
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是自然之法。在此姑且将之称为无限责任。而有限责任则是源起于商业活动中商人规避风险的需求,即以特定的财产承担限定的责任。所以无限责任本就是责任的一般情况,有限责任才是因约定或法定而生的例外情况。
法谚云:人皆不必承担他人行为的后果。即每个人仅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除非法律另有特别规定。自然人以外的实体因法律规定而成为法律上的人,自此法人的经营活动就只是法人自己的行为而非其经理或投资人的行为,所以应由法人以其全部财产自行承担责任,自然无需经理或其投资人承担责任。
就信托而言,由于信托并没有法人资格,信托财产的名义所有人及处理信托事务的人均为受托人,所以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仍旧是受托人自己的行为,当由受托人承担行为的后果。由于受托人毕竟是为受益人的利益而行为,所以受托人就其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信托财产追偿。故信托对外责任的传统规则是,信托的责任财产首先是信托财产,但不限于信托财产,当信托财产不足以清偿信托债务时,受托人应继续以其固有财产进行清偿,即受托人对信托债权人承担无限责任。
轻资产的商业信托受托人管理着远超于其财产规模的信托财产,对外承担无限责任对其而言显然是一种难承其重的风险,所以资产管理机构往往会通过事先约定的方式寻求免责,正如文首提到的“资管产品仅以其财产为限承担责任”。
随着商业信托的发展,“管理人有限责任”的约定出现了法定化的倾向。日本信托法第21条第2项列举了4种仅以信托财产对外承担债务的情形,其中就包括受托人与信托债权人约定的情形。此外,还在第216条规定了“限定责任信托”的特殊信托,以供受托人选择适用。美国现代信托法走得更远。美国统一信托法典(“UTC”)第1010条规定,除合同另有规定外,对于在管理信托过程中以受托人的身份采取适当方式订立的合同,如果受托人披露了自己的受托人身份,则受托人对该合同不承担个人责任。即原则上受托人对外不承担个人责任,除非另有约定。随着UTC被大多数州通过,可以说美国法已彻底转变了受托人对信托债权人承担无限责任的传统立场,其中,明尼苏达州等州的实体法更是承认了商业信托的法人资格。
从日美两国的信托法可见,受托人有限责任都依赖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这也印证了受托人有限责任必须基于约定或法定的观点。就我国而言,如上文所述,信托法第37条并不能推导出受托人有限责任的结论。且信托也不符合民法典规定的法人构成要件,不能以自己的名义订立合同、实施交易行为、起诉与受诉。因此,我国的立场仍然是受托人原则上对外承担无限责任,除非与信托债权人进行了免责约定。
结论
综上所述,就本文开始提到的问题,资产管理人并不享有法定的有限责任,当“特殊单位客户”无法向期货公司承担责任时,管理人应负继续清偿的义务。在期货经纪、场外衍生品交易等业务中,资产管理人主张约定“管理人有限责任”,将缩减责任财产的范围,不利于期货公司维护自身利益。而在资产管理业务中,“管理人有限责任”对期货公司而言则属于有利条款。因此,对“管理人有限责任”的扬弃取决于业务场景。值得一提的是,责任的约定本质上属于风险的事先分配。所以,如果一旦接受了“管理人有限责任”,更应对业务持续加强风险管理,通过风控措施避免发生信托财产不足以承担责任的情形。